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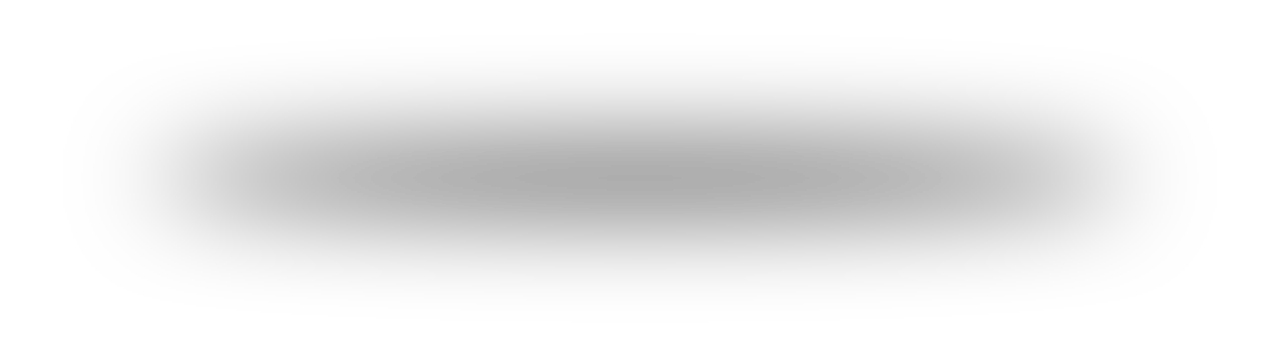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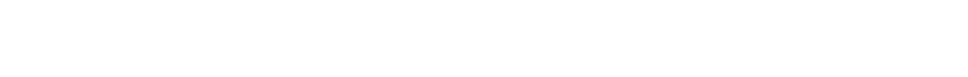
霍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徇私枉法罪、受贿罪
[关健词] 诈骗 诈骗数额认定 既遂时点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毕某,男,195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原系重庆市某区西城街道新桥村村民。2013年1月5日因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8日被依法逮捕。
某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某犯合同诈骗罪,于2013年10月11日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某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毕某于2000年始,长期占用某区某小学的校舍,从事个体经营。2002年,因张某无房居住,通过毕某与该校联系,以4000元价格购买了该校空置的校舍。2006年6月,毕某为了获取张某已购买的校舍之一部分,从张某处借出买卖房屋协议书原件,经复印后,在该复印件上涂改并将买受人张某改成毕某,又重新复印。从而伪造了毕某购买某小学校舍的虚假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2007年2月,某区土地房屋管理局发布征用包括毕某所居住区域在内的土地 的公告,毕某即以其是征地拆迁范围的被拆迁人,要求给予拆迁安置补偿。同年12月,毕某与其子女制定分家协议一份,将其虚假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房屋分给其子女。2008年1月间,毕某之子女与拆迁安置机构分别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毕某之子女分别获得拆迁补偿款195000余元和安置房9套(包括门面3套)。根据某区征用土地安置管理办法,被拆迁人应按照政府的统一规划,集中进行安置房建设,建设费用由被拆迁人自行承担,并以委托建房方式委托政府指定的建设方建设,其应支付的房屋建设费用采取“委托建房款”方式支付。2008年1月、2010年12月,毕某通过其子女向拆迁安置机构支付了联建房屋款项(即委托建房款)52余万元。2010年12月20日,毕某通过政府集中联建房屋竣工,并交付给毕某占有使用。
案发后,司法机关对毕某取得的6套房屋,鉴定意见为安置房屋总价为1068000元,加上货币补偿款95000元,共计补偿金额为1163733元,扣除毕某支付的委托建房款520634元,毕某共骗取国家安置补偿款64万余元。
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查明的事实与某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事实基本一致。
某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毕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国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第52条、第53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毕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毕某所获赃款六万余元。
毕某不服一审判决,以原判认定诈骗数额有误,量刑过重,向二审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出庭检察人员也认为,原判决认定诈骗数额有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不当,建议二审法院改判。辩护人提出了认定诈骗数额错误,不应把毕某骗取拆迁安置资格后自己投资建设的房屋之相应价值认定为诈骗数额,其诈骗金额仅为直接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款195000元;司法鉴定以2012年12月20日作为诈骗既遂的时点,并以此时点进行房屋价格鉴定是错误的。毕某自2008年1月与拆迁机构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时即为犯罪行为既遂,按照刑法连续犯之理论,鉴定时点应界定在2008年1月。对毕某犯诈骗的量刑过重,应给予纠正。
二审人民法院对认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维持了原判决。
二、主要争议问题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
1、被告人毕某依照某区关于拆迁安置房屋集中联建,并由被拆迁人支付建房款的规定,毕某所支付的委托建房款是否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
2、被告人毕某的犯罪行为是何时既遂,对其取得的房屋应以何时作为计算房屋价值的时点?财产性收益是否应认定为诈骗数额?
三、辩护要旨
本案在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对被告人毕某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获得了拆迁安置补偿资格,直接获得了国家给予的房屋补偿价款人民币19万余元的基本事实无争议,唯对被告人毕某依照某区的有关规定,在骗取拆迁安置资格后,自己投资建设了安置房屋是否应当认定为诈骗数额?被告人毕某在2008年1月与某区拆迁安置机构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是否即为犯罪行为既遂,若对被告人毕某取得房屋进行价值鉴定,是应以2008年1月为准,还是应以其实际取得房屋的2012年12月为准?存在较大争议。现法律分析于后。
(一)被告人毕某采取欺骗手段获取拆迁安置资格,依照某区的相关规定,自己投资建设的安置房屋不应认定为诈骗财产(数额)
首先,根据某区制定的“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被拆迁人应按照“七统一分”(统一地址、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用地、统一质量管理、统一建设管理、统一基础设施和建房费用自理、联建费用分摊)的要求,在集中联建安置点划地建房。被告人毕某通过其子女取得拆迁安置建房的资格后,自己出资并交由统一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建设。被告人毕某仅是通过虚构房屋买卖协议的犯罪手段,获取了在集中联建安置点自建住房的资格,而非骗取了国家财产。
其次,根据被告人毕某通过其子女与拆迁安置机构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拆迁安置交接房协议书等的相关约定,被告人毕某应支付自建房屋价款504073元,加上被告人应补交的防盗门差价,被告人毕某共计支付委托建房款520536余元,缴纳了自建安置房的房款。
再次,被告人毕某通过虚构房屋买卖协议的犯罪手段,获取的在集中联建安置点自建住房资格,不具有财产性质,不能将此认定为诈骗犯罪的数额。
因此,被告人毕某自己承担的全额房款不应认定为诈骗犯罪的数额。
(二)关于诈骗既遂的时点问题。
一、二审判决均认为,认定被告人毕某诈骗犯罪完成的时点为2012年12月,鉴定应当以此时点为准。
该认定是极其错误的,其理由是:
假设被告人毕某修建的房屋应认定为骗取国家财产的行为,则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及相关刑法理论,被告人毕某的诈骗行为于2008年1月即已完成,是既遂行为。其于2012年12月才接收房屋的行为,是刑法理论上的继续犯(又称持续犯)行为。
继续犯(又称持续犯)是指一个已经实现犯罪既遂的行为,在相当既遂后的相当时间内持续侵犯同一或者相同客体的犯罪。继续犯的三个显著特征为:(1)继续犯是犯罪既遂后犯罪状态的继续;(2)继续犯是在持续地侵犯同一客体或者相同客体;(3)继续犯须有一定的持续时间。状态犯是指犯罪行为完成时,犯罪行为即告结束。但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不法状态或者结果仍处于继续状态。犯罪既遂的基本构成条件是,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全部符合其所实施之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被告人毕某在取得房屋集中联建的“权利”后,就已经具备了必然获取住房、门面的之结果。至于何时取得,则仅是犯罪行为的不法状态的延续,并非犯罪行为没有既遂。至于持续状态后,房屋因市场价格而发生的价值变化,影响到财产收益的变动,则不应以该财产收益认定为诈骗数额。
一、二审判决以2010年12月作为诈骗既遂时点,进而以此作为司法鉴定时点显然是错误的。一、二审判决所认定诈骗数额的主要依据即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
最新动态
- 荣誉 | 坤源衡泰入选律新社《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4):破产领域》律所名录,赵粹李律师获“实力律师”称号 2024-08-12 00:00:00
- 棒棒哒!坤源衡泰王若玉、吴兰兰律师在“首届云贵川渝桂藏青年律师辩论大赛”中分别荣获“最佳辩手”“优秀辩手” 2024-08-05 00:00:00
- 荣耀时刻 | 坤源衡泰辩论队荣获首届重庆市青年律师辩论赛季军,两名律师荣获“最佳辩手”、“优秀辩手”称号 2024-06-05 00:00:00
- 荣誉 | 坤源衡泰连续三年荣登Benchmark Litigation中国区域榜单 2024-06-04 00:00:00
- 荣誉 | 坤源衡泰荣任重庆市企业破产案件一级管理人 2024-05-24 00:00:00
- 荣誉 | 坤源衡泰与西政共同建设的民法典国民教育科普基地获评2023年度重庆市人文社科普及基地先进单位 2024-02-07 00:00:00
- 重磅 | 连续5年!坤源衡泰再度载誉钱伯斯大中华区榜单Band 1 2024-01-18 00:00:00
- 重磅 | 本所主任何洪涛律师当选重庆市律师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 2023-12-21 00:00:00
- 荣誉 | 本所再次获评重庆市优秀律所,王斌律师荣获重庆市十佳律师 2023-12-19 00:00:00
- 荣誉 | 坤源衡泰卢代富、谢鹏律师深度参与的项目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2023-12-13 00:00:00



